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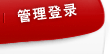 |
|
爱因斯坦的机遇与眼光
更自由的眼光使他抓住了时代的机遇
26岁的爱因斯坦敢于质疑人类关于时间的直觉观念,从而打开了通向微观世界的新物理学之门。
1905年通常称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奇迹年”。在那一年,爱因斯坦引发了人类关于物理世界的基本概念(时间、空间、能量、光和物质)的三大革命。一个26岁、默默无闻的专利局职员如何能引起如此深远的观念变革,因而打开了通往现代科技时代之门?当然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我们也许可以分析他成为这一历史性人物的一些必要因素。
首先,爱因斯坦极其幸运:他出生于合适的时代,当物理学界面临着重重危机时,他的创造力正处于巅峰。换句话说,他有机会改写物理学的进程,这也许是自从牛顿时代以来独一无二的机遇。这种机遇少之又少。E.T.贝尔的《数学精英》引用了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的话:“虽然牛顿确实是杰出的天才,但是我们必需承认他也是最幸运的人:人类只有一次机会去建立世界的体系。”
这里,拉格朗日引用的是牛顿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第三卷即最后一卷前言中的话:“现在我要演示世界体系的框架。”
拉格朗日显然非常嫉妒牛顿的机遇。可是爱因斯坦对牛顿的公开评价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幸运的牛顿,幸福的科学童年……他既融合实验者、理论家、机械师为一体,又是阐释的艺术家。他屹立在我们面前,坚强、自信、独一无二。”
爱因斯坦有机会修正200多年前牛顿所创建的体系。可是这个机会当然也对同时代的科学家们开放。的确,自从1881年迈克尔逊-莫雷首次实验以及1887年第二次实验以来,运动系统中的电动力学一直是许多人在钻研的热门课题。令人惊奇的是,当爱因斯坦仍在苏黎世念书时,他已经对这个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99年他曾写信给他后来的太太米列娃:“我还了赫姆霍兹的书,现正在非常仔细地重读赫兹的电力传播的著作,因为我以前没能明白赫姆霍兹关于电动力学中最小作用量原理的论述。我越来越相信今天所了解的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与实际并不相符,而且可能有更简单的理解方式。”
他追寻此更简单的理解方式,六年以后提出了狭义相对论。
当时许多科学家对这个课题也极感兴趣。庞加莱是当时两位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也正在钻研同一个问题。事实上,相对性这一名词的发明者并不是爱因斯坦,而是庞加莱。庞加莱在1905年的前一年的演讲《新世纪的物理学》中有这样一段:“根据相对性原则,无论是对于固定不动的观察者,或是对于作匀速运动的观察者,物理现象的规律应该是同样的。这样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辨别我们是处于静止还是处于匀速运动状态。”
这一段不仅介绍了相对性这个概念,而且显示出了异常的哲学洞察力。然而,庞加莱没有完全理解这段话在物理学上的意义:同一演讲的后几段证明他没有抓住同时的相对性这个关键性、革命性的思想。
爱因斯坦也不是首位写下伟大的相对论变换公式的人。之前,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曾写出这个公式,所以当时这个公式以洛伦兹变换命名,现在仍然是这样。可是洛伦兹也没能抓住同时的相对性这个革命性思想。1915年他写道:“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死守一个观念:只有变量才能作为真正的时间,而当地时间仅能作为辅助的数学量。”
这就是说,洛伦兹有数学,但没有物理学;庞加莱有哲学,但也没有物理学。正是26岁的爱因斯坦敢于质疑人类关于时间的直觉观念,坚持同时是相对的,才从而打开了通向微观世界的新物理学之门。
几乎今天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同意是爱因斯坦创建了狭义相对论。这对庞加莱和洛伦兹是否公平?要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先引用英国数学家怀特海的话:“科学的历史告诉我们:非常接近真理和真正懂得它的意义是两回事。每一个重要的理论都被它的发现者之前的人说过了。”
洛伦兹和庞加莱都没有抓住那个时代的机遇。他们致力于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即运动系统中的电动力学,可是他们都错失良机,因为他们死守着旧观念,正如洛伦兹自己后来所说的一样。爱因斯坦没有错失良机是因为他对于时空有更自由的眼光。
要有自由的眼光,必须能够同时近观和远看同一问题。远距离眼光这一常用词就显示了保持一定距离在任何研究工作中的必要性。可是只有远距离眼光还不够,必须与近距离的探索相结合。正是这种能自由调节、评价与比较远近观察的结果的能力形成了自由的眼光。按照这一比喻,我们可以说洛伦兹失败了是因为他只有近距离眼光,而庞加莱失败了是因为他只有远距离眼光。
|
|
|
|

|
|
|
 苏公网安备32041202001011
苏公网安备32041202001011